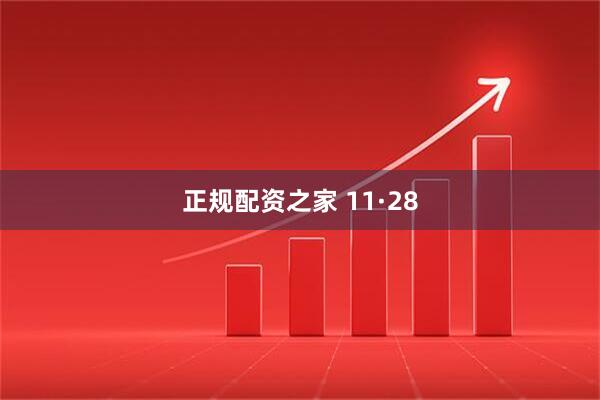1947年夏天,豫鄂皖交界的大别山深处,一支穿插部队悄然向北移动。山路崎岖,枪声零星,却从未真正停下。刘伯承、邓小平率领的刘邓大军主力已经突破防线,而在后方长沙股票配资,大别山的一支中原独立旅,正在为这支大军守住一条生命线。旅里一位副旅长,满身尘土,整夜未合眼,嘴上却一直念叨着一句话:“大别山红旗不能倒,枪声不能停。”
这个副旅长,叫罗厚福。八年抗战,三年解放战争,他几乎从未离开大别山及中原地区的斗争一线。1955年,授衔时他只戴上了大校肩章,却佩戴了极少数人才拥有的三枚一级勋章:一级八一勋章、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。在上千名将官中,大多只是将领才有此荣誉,而他,是当中唯一一位大校。
有意思的是,这样一位历经土地革命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的老红军,在很多人记忆里却很陌生。他出生在湖北黄安,一个地道的贫苦农家,走上革命道路时不过二十岁,却一步步把自己的人生,写进了中国革命最艰苦的一段历史里。
一、从赤卫队连长到红二十八军营长:大别山里“死里逃生”的干部
1909年,罗厚福出生在湖北黄安(今红安)。这个地方后来出了多少将军,已经无需多说。到1929年前后,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兴起,他也和很多同乡一样,参加了本地的赤卫队,开始拿起枪走上革命道路。
赤卫队其实算不上正规军,装备差,训练也谈不上标准,可仗打得真。罗厚福在战斗中大胆又稳,屡次立功,不到几年,就被任命为连长。这种从最底层打上来的干部,在红军里并不罕见,却往往最能耐得住艰苦。

1932年,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发动大规模“围剿”,形势一下紧张到了极点。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,一些部队被迫转移。就在这种时候,党组织给罗厚福下达了一个危险的任务:潜回麻城一带寻找失散的组织,重建党和苏维埃政权。
这不是简单的“找人”。当时敌人封锁严密,白区环境极其险恶,一不小心就是掉脑袋的事。罗厚福按照命令回到原地区,辗转联络,慢慢恢复起第五区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,把散落的革命火种重新聚了起来。这段经历很少被提起,却是衡量一个干部能不能扛事的关键时刻。
被重新整合的部队,又在革命风雨中走向新的阶段。1935年2月,红二十五军西征后留在鄂东北的部队,与鄂东北独立团合编成红二十八军,高敬亭任政委。这支红军,在整个鄂豫皖地区,算是一支“留下来打”的部队,而不是随主力长征远去的那支。罗厚福所在部队被编入红二十八军,他被任命为营长。
正是这支红二十八军,在之后的岁月中,扛起了“大别山红旗不倒”的历史任务。但在敌人围追堵截之外,更麻烦的是内部的“左”倾错误。
有一段经历,让很多了解内情的人一直记着。红二十八军内部搞肃反时,一度出现严重偏差,不少无辜干部战士被错杀、冤杀。罗厚福看在眼里,急在心里。有一天,他忍不住找到肃反委员会负责人,当面质问这种乱抓乱杀的做法,说得很重,也很冲。
肃反保卫部门的负责人听在耳里,怒在心中。不久,罗厚福就被以“有问题”为名拘捕。审讯中,他被反复追问所谓“派别活动”,他只说了一句:“我是共产党员,没参加什么派。”这一句,顶住了压力,也透露出当时环境的紧张程度。

押赴刑场的路上,情况突然变了。部队遭遇敌袭,队伍被打乱,罗厚福在混乱中脱险。很多人可能会选择脱离部队、另谋出路,他却没有。逃过一劫后,他没有远走他乡,而是重新回到了大别山,继续拉队伍,坚持游击斗争。
土地革命战争时期,他先后担任过连长、中共光山县委书记、鄂东北道委第三路游击师师长等职,在大别山及周边地区坚持了长达三年的游击战争。这些职务里,师长这个级别,正是后来评定一级八一勋章的重要依据之一。
级别是其一,更重要的是在险境中始终不散,带着一支支小部队在山林间周旋。这种熬得住、扛得起的干部,在战争年代极其宝贵。
二、从新四军到中原突围:大别山红旗不倒的“硬骨头”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,红二十八军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,整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,高敬亭任司令员。这时的大别山,已经从内战的一个根据地,变成了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罗厚福在这一时期,历任新四军第六游击大队大队长、新四军第五师十四旅旅长、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等职。职务不断提升,但地盘却依旧是那片山,那些沟壑,那些敌人的封锁线。
在抗战中,大别山地区的局势极其复杂。这里不仅有日军和伪军,还有国民党顽固派的围堵和掣肘。一边打日本侵略者,一边还要防备来自背后的干扰。罗厚福率部在这片区域,日夜拉锯,打掉不少日伪据点,多次粉碎日军“清乡”“扫荡”。

不少战斗,规模不算大,却极为凶险。有的小据点打一夜就结束,真实战果却往往体现在一个区、一个县能不能继续坚持下去。试想一下,一旦这些根据地被连根拔起,整个华中抗日局面的稳固,就会大打折扣。这种作用,在地图上并不显眼,但在整个抗战格局中却很关键。
抗战胜利后,根据中央部署,新四军、八路军整编为野战军和地方军区部队。罗厚福先后担任江汉军区副司令员、鄂西北军区副司令员、中原军区独立旅副旅长等职。此时,中原地区已成为国共双方争夺的焦点。
1946年,中原军区部队在极端艰苦条件下被迫开展中原突围。国民党军队重兵包围,企图一战吃掉中原解放军主力。罗厚福所率部队,担负的是相当危险的任务——掩护主力突围。
那一年的夏季,中原地区闷热潮湿,部队粮弹紧缺,行军多在夜间进行。罗厚福率部阻击、佯动、穿插,一步步把敌人的注意力往自己身上引。到1946年8月,中原军区主要部队陆续突围成功后,他率部与南路突围主力在湖北房县会合,组建了鄂西北军区,他出任副司令员。
敌后作战的难度,到了这一时期更为突出。没有稳定补给,敌人重兵封锁,地方武装杂乱,环境比早年游击战更为复杂。他们一边坚持武装斗争,一边开展土地改革和地方政权建设,把根据地连成片,为后来的全国性战略反攻打下了基础。
1947年,中原局势再度变化,部队编制调整。罗厚福所在部队整编为中原独立旅,他担任副旅长。这支旅不久后成为刘邓大军的直属独立旅,是机动性很强的一支劲旅。
刘伯承、邓小平到部队视察时,对罗厚福说过一句话:“大别山红旗不倒,枪声不断,你罗厚福有很大的功劳。”这句评价,在懂行的人看来分量很重——不是泛泛而谈,而是点名强调他在大别山长期坚持斗争的作用。

这段经历,也是罗厚福后来获得一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一级解放勋章的重要依据。抗战时期的旅长、军分区司令员,解放战争时期的军区副司令员、独立旅副旅长,级别、战果都摆在那里,绝不是凭空拔高。
三、授衔时的大校与三枚一级勋章:功劳、处分与评价
1949年全国解放后,罗厚福转入地方和军区机关工作,历任湖北军区副参谋长、军区干部部部长等职。战火渐息,很多老红军开始面对新的考验,不是枪林弹雨,而是制度与纪律。
1951年,他受到过严重处分,被行政降职,并给予党内警告。原因主要有两件事。
一件是与军区自办工厂有关。当时,国家经济基础薄弱,各地军区为了减轻负担,在一定范围内自办了一些小工厂。罗厚福所在军分区,为了解决经费和后勤问题,按照他的主张,自筹资金办厂。他号召干部拿出个人积蓄做垫资,工厂盈利后,再按比例给这些干部返利。
这种做法,在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下,很容易被理解为搞“分红”、搞小集体经济。尤其是在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政治氛围下,此举被认定为严重错误,影响很坏。不得不说,他在政治上的敏感度,在这一点上出现了明显偏差。

另一件事看起来则完全不同。战争时期,有一位当地保长暗中掩护过我党我军的同志,多次出手营救,属于隐藏在敌人统治区的“开明保长”。解放后,当地政府不明内情,准备按一般“保长”处理,定性为与敌人合作的反动分子。对这位保长来说,这几乎是难以翻身的打击。
保长慌了神,跑到罗厚福所在的军分区求助。了解情况后,罗厚福出面替他作证明,表示此人曾多次冒险保护革命同志,不能一概而论。后来的结果,是他不仅保住了这位保长的命,还安排他到烟厂当工人。
这件事,从党纪角度看,是“包庇保长”;从人情和实际贡献看,又是出于对一位实有功劳者的保护。组织上把这两件事合并起来,给予严肃处理,这在当时政治环境中可以理解,却对他此后的仕途和授衔产生了不小影响。
1955年,全军开始实行军衔制,并大规模评定勋章。根据当年的评定办法,一级八一勋章主要授予红军时期的师级以上干部;一级独立自由勋章授予在八路军、新四军中旅级及相当级别以上的干部;一级解放勋章则授予解放战争时期军级及相当级别的干部,以及领导整军起义有功人员。
在上千名被授予少将、中将、上将乃至元帅军衔的军官中,同时戴上三枚一级勋章的,共有一百四十余人,都是经历了三大时期、多次大战的老将。像李天佑、杨至成这样的著名上将,都没有三枚一级勋章在身,由此可见标准之严。
罗厚福的情况,很特别。按照职务和资历,他红军时期担任过游击师师长,抗战时期是新四军旅长、军分区司令员,解放战争中任军区副司令员、独立旅副旅长,从职级上看,完全符合三级一线的勋章授予条件。于是,评勋章时,他获授一级八一勋章、一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一级解放勋章。
然而,在军衔评定时,他受到过的处分、政治评价中的“瑕疵”,很难不被考虑。结果就是——他只被授予大校军衔,却同时佩戴三枚一级勋章,成为全军极少见的特殊案例。

也正因为如此,许多当年与他一起浴血奋战的将领,在看到授衔名单时,都感到很意外。《大别山的儿子》一书中有一篇《中将的军礼》,提到一件往事:那是在一次惨烈战斗后,战场上躺满了牺牲的战士,烟尘未散。有人劝罗厚福:“别回去了,太危险。”他执意要折回去搜寻,“说不定还有活着的。”
他在一堆阵亡战士遗体中翻找,终于背出一个还剩一口气的小通讯员。多年后,这名小通讯员在1955年被授予开国中将军衔,后来还担任过大军区的领导。授衔那年,他得知自己的老领导只被评为大校,简直不敢相信,久久无语。
1961年,罗厚福军衔晋升为少将。这时他已经五十多岁,历经战火和政治起伏,对自己的荣辱看得相当平淡。他曾说过一句颇为朴实的话:“党教育了我,人民养活了我,离开了组织和人民,哪有我罗厚福哟!”这句话没什么华丽辞藻,却很能反映一个老红军的心态——个人遭遇固然在意,却没有把个人得失看得比组织更重。
在熟悉他的人心中,对他的评价也相当明确。李先念对他有一句高度概括的话:“是一个没有掺假的农民,是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。”所谓“没有掺假的农民”,不是说他土,而是说他身上那股子直、那股子真,贯穿始终。该顶的时候,他敢顶;该认错的时候,他也认。
罗厚福的一生,起落并存。土地革命时期被错误关押、押往刑场路上死里逃生;抗战、解放战争中屡次立功,却在和平年代因为两件事受到严厉处分;授衔时军衔偏低,却戴上了含金量极高的三枚一级勋章。这样的履历,不难说传奇,也不算顺遂。
1975年,他在武汉病逝,终年六十六岁。大别山的山风依旧,许多与他并肩战斗过的老战士,提起他时往往只说一句:“这个人,心里有杆秤。”这杆秤,衡量的是革命的大局,是群众的冷暖长沙股票配资,也衡量着他自己脚下走过的那条路。
海信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